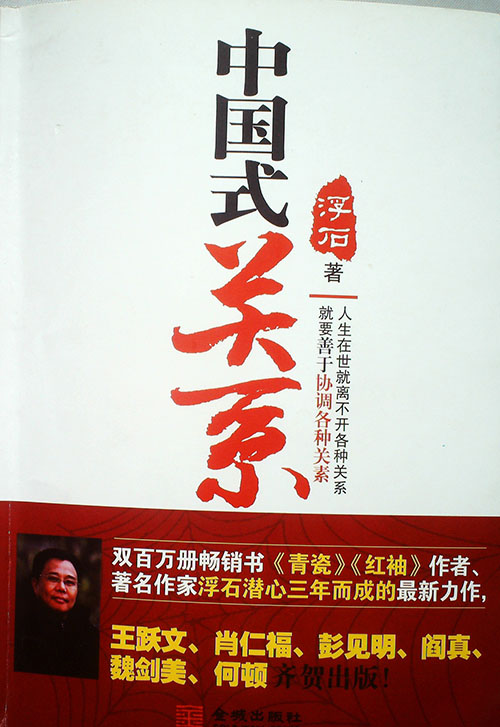共计 2582 个字符,预计需要花费 7 分钟才能阅读完成。
衙门与衙门作风
郭君臣、刘广两先生写过一本叫《衙门》的书,很有趣味,让我们对耳熟能详的衙门一词有了更多和更深的了解。
衙门是旧时官员办公的机关,是中国民间对于官府的称呼。在老百姓心目中,提及衙门肯定心情复杂,因为它隐藏着人们对于官府的敬畏、羡慕和厌恶。
据说,衙门实为牙门。
没错,是爪牙的牙,也是武装到牙齿的牙。这是怎么来的呢?原来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打仗的将军就已经被称为国王的爪牙,那时的将军们常把一些猛兽的爪或牙置放在指挥场所最显眼的位置,最初的动机也许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战利品,就像现在的官员还在热衷的什么什么成果展,似乎有向国王邀功请赏的意思。慢慢地,将军们开始以爪牙自居,也以充当爪牙为荣。这是将军们对上面、对国王的态度,对下或对外,情况则有所不同,揣摸将军们的意思,可能有两层,一是我为爪牙,看你怕也不怕;二是凶禽猛兽都已被我饮其血食其肉,看你怕也不怕,总而言之是为了耀武扬威,通过看得见的道具让人把自己与凶猛的嗜血动物发生关联,以便让你心生畏惧。在这一点上,类似于现代军事上的武装演习与公布成功进行了一次核实验的消息。
到后来,为了省事和显眼,也可能是凶禽猛兽经不起杀戮越来越少,将军们干脆在军营门口的旗杆上雕饰出大型的兽牙,自此营门便有了牙门的别称。到了南北朝时期,官署之门开始被叫做衙门。
那么,到底是怎么从牙门到衙门的呢?对此我没有研究,真要究其缘由,则可能是这样——那时常有一人身兼文官武将的情况,本为军人者很容易把武风带人官府,此时把牙齿、牙旗直接带人官府显然不妥,便来了个含蓄表述,由牙到衙,以显示自己尚通文墨。文人出身者为避免被人看成文弱书生也得附庸武风,于是大家慢慢地达成了共识,都觉得牙门两个字虽然具有很好的形象识别功能,且总有一种威风凛凛的精神风貌,能够让人立马生出怯意,但似乎真的没必要那么张牙舞爪,按照做人要直、白、浅,作文要曲、隐、深的追求,还是以衙含蓄表达吧。
旧社会的衙门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场所,它有时候也被称之为官场。
衙门八字开,有理无钱莫进来。破家的县令,灭门的知府,说的都是它所具有的威慑力量,所以,平头老百姓除了默默地忍受它的盘剥与搜刮,便只有历朝历代做清官梦的分儿,并尽量避免与衙门发生关系与纠葛,因为衙门拥有的力量是如此神秘而强大,一且与它牵扯上,肯定是鸡蛋碰石头,不死也要脱层皮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再老实本分的良民,不得不进衙门或者见官的时候,也总是会忍不住心惊肉跳腿抽筋。
衙门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,因为它是官儿们扎堆办公的场所,在里面上班的人都是一人或几个人之下多少多少人之上,足以让他傲视芸芸众生。他们手里紧握着权力,判官断案,控制着他人的生死命运,因为旧社会天高皇帝远,信息闭塞而极不对称,当官的便自然拥有了很大的“自由裁量权”,有时候甚至可以为所欲为。在万恶的、吃人的旧社会,你要么统治别人、控制别人,要么被别人统治、控制,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企图混进衙门。
等到真的进了衙门,才发现情况要复杂很多,这里不仅满是结党营私的权力斗争和权钱交易的重重黑幕,更是丑恶人性与丑陋行径的展示舞台;既有玩弄同类于股掌之中的权力与可能,也充满宦海沉浮的不确 定性;既能让你平步青云,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也能让你一脚踏空,满门抄斩。
不过,总体来说,人们对衙门的恐惧,比之衙门对人的诱惑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因为如果成不了衙门中人,情况将更为糟糕。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,如果那样,你的命运将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。打个比喻来说,你手里有枪,不一定会去射杀别人,但见你手里有枪,想射杀你的人,便多少会有些顾忌。
衙门里的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的,《衙门》一书的前言中说:“衙门里也会有一些改变弊端的努力或呼声,大者如杜甫,于困苦的战乱流浪中不忘‘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’。这样的儒家政治信念可谓源远流长,那些想成为官员的士大夫一般是在这种理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。像杜甫一样向往着‘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,的士人不在少数,但政治理想往往和现实利益或具体境况纠缠不清,我们能看到很多文人在官场中大志难酬的幽愤和受到压制的郁闷。胸怀理想的官员很难忍受衙门里的逢迎、争斗和不知羞耻的腐败、压迫,于是常想象着要归隐山林,或者干脆像陶渊明那样弃官而去,‘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’,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’。”
应该庆幸现在已经没有衙门了,现在有的只有各级党政机关和政府部门,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,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,所以,一旦个别官员不称职、搞贪腐,不仅老百姓可以公开地仇视他,可以在网上人肉他,可以在舆论工具上媒治他,组织部门还可以罢免之,纪检部门还可以双规之,政法部门还可以法办之。
当然,我们也要看到,毕竟衙门有着几千年的历史,衙门不再,衙门作风却不大可能在一个早晨消失殆尽。这几年为什么官场文学长盛不衰?除了普通老百姓对所谓的官场有着强烈的探求欲、窥视欲之外,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,就是许多官场中人,身在官场,却常常有着类似于杜甫、陶渊明式的感受,他们很有可能在官场文学中的主人公身上找到了或多或少的共鸣。
这是值得庆幸的,也是让人可怕的。
庆幸的是,毕竟官场中还有众多的人良知未泯,有危机意识,尝试着整顿机关作风。可怕的是,数百年数千年过去了,人们对官僚机构的感觉,似乎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。
还是让我们再引用《衙门》一书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吧:“衙门是处于皇帝和百姓之间的官僚机构,却使得百姓和有理想的官员很不舒服,并且使官员规律性地走向腐化,变得暮气沉沉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是缺少高明的政治思想,以至于官僚只能屈从于自己的欲望?还是官僚结构不够完备,使得钻空子成为习惯?”我们这才发现,对于衙门,“除了惊心、无奈于它的黑暗之外,我们还需要知道更多。”
公正而客观地说,现在的官僚作风已经少多了,已经好多了。它的表现已不再是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,而是曲里拐弯、袖里乾坤、顾左言右,不直截了当地说行,也不明确无误地说不行,而是采取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,“哼”,“嗯”,“研究研究”,以便为事情的暗箱操作预留下广阔的腾挪空间。
也正因为如此,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,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,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,让行政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。从比较无奈或消极的意义上来说,为了与时俱进,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探索新的潜规则予以适应或化解。